相隔一个月,魏书钧的《永安镇故事集》与《河边的错误》相继上映。《永安镇故事集》在不久前公布的金鸡奖提名名单中获得四个提名,足见业内对魏书钧能力的认可。只不过,《永安镇故事集》票房遇冷,三百万出头的票房令人遗憾。《河边的错误》总算可以让投资方放心了,改编自余华的小说+朱一龙领衔主演+平遥电影节大放异彩,让这部文艺片获得很高的市场关注度,首日票房突破5000万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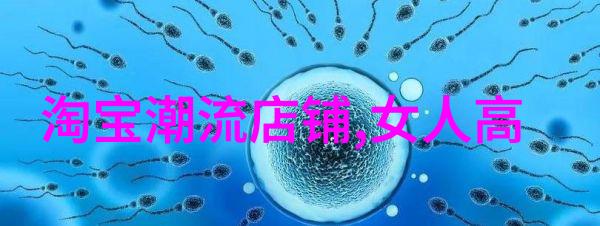
《河边的错误》海报
《河边的错误》改编自余华发表于1988年的同名中篇小说。此时是余华创作的早期阶段,小说带有非常鲜明的先锋属性,看着像悬疑侦探小说,实际上反类型、反逻辑、反理性。也由此,虽然张艺谋等大导演都曾萌生将小说搬上大银幕的想法,又纷纷作罢。直到2020年,电影改编项目来到魏书钧手中,剧本启动,2021年电影开拍。
诚如编剧康春雷所言,“原来的小说实际上是通过办案对生活做了一个比喻,而电影应该直接把生活切入进来”。剧本对余华的小说做了很大的改编,尤其鲜明的是剧情前半程对于类型元素的凸显。所以,有些观众看前半程时,多少会觉得这有点像199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《杀人回忆》。
1990年代中期的一个江南小镇,一位老婆婆在河边被谋杀,马哲(朱一龙 饰)负责案件的侦查。他一一排除可能作案的嫌疑人,最终锁定老婆婆领养的疯子(康春雷 饰)。案件本该就此结束,但一些疑点的存在让马哲打算一查到底,与此同时,疯子跑出疯人院继续作案让马哲再度陷入紧张,他的精神状态发生剧烈变化……
马哲探案的过程,比如他排除几个目击者的犯罪嫌疑,遵循的是刑侦探案剧的逻辑,通过技术勘验、人员走访、口供追查等手段不断去接近。尤其是通过录音带中火车的鸣笛声推断出录音带的主人这一过程,很好体现了马哲经验的老道。
商业片观众就此对电影抱着中国版《杀人回忆》的期待,在电影的中后段时,可能会陷入失望。电影的中后段进入心理悬疑环节,有大量主观意识流桥段,文艺腔调十足。也是在这一部分,电影延续了余华小说中关于“癫狂与理性”的思索。可以说,电影的改编是融入类型元素,调整小说中更大尺度的书写,精神内核并未有本质上的变动。
中后段的剧情概括起来就是——马哲“疯”了,影像真实与虚拟的边界开始模糊。
观众无法准确判定马哲是在某个时间“疯”的,或者是否真有什么前兆——比如他在云南时是否获得三等功的疑云。不过,在那段充满导演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梦境之后,观众逐渐察觉电影真实与虚拟边界在发生模糊,弹匣里完整的7颗佐证了马哲已经陷入意识上的混沌。
哪怕观众错过导演以上的全部暗示,经由朱一龙的出色表演,观众可以直观察觉到马哲的灵魂在渐渐飘散,他的精气神逐渐被抽干。电影采取的是顺拍,为了更好体现角色精神状态的变化,朱一龙先增肥30斤,随着剧情的推进他的体重又慢慢降低了20斤。伴随着身体这种“准确”的消瘦,马哲眼神里的果决、笃定慢慢变少,取而代之的是呆滞、空洞和死板。
朱一龙的表演很好带动了观众去感受角色的变化,电影之外我们却不可避免需要试着条分缕析马哲“疯”了的原因。到底,马哲为什么“疯”了?
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肯定是一方面。电影中的马哲经常熬夜加班,家很少回,烟不离手,精神上处于高度紧绷、高度疲惫的状态。疯子外逃并继续作案,警局面临着上级施加的压力,马哲承受更大的焦虑。紧绷的弦往往无比脆弱,或加剧精神危机的发生。
更致命的,是理性的崩塌。作为局里的破案主力,马哲经验丰富,工作认真,对案件的每个疑点有很深的执着,也自然地,他崇尚与践行的是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严谨推理。甚至,他对有一种不自知的乐观,认为侦破案件、突破每个疑点,才是负责任,也必然会带来“好”的结果。
但河边的案件,让马哲信奉的理性遭遇挑战。他费了好大波折从录音带找到逃跑的目击证人,一个女会计和她深爱的诗人,但他俩都排除了嫌疑,一切努力像无用功。
接着从诗人的口中,又得知了他在河边看到一个烫着大波浪头的纺织厂女工,可那个时间段走出纺织厂的只有一个叫许亮的男理发师。这个烫着大波浪头的女人是谁?还没找到头绪,诗人就死在河边。马哲的无力感此时已经逐渐凸显——如若不是诗人的秘密被自己发现,会否他就不会死?
一筹莫展之际,疯子突然现身,手拿凶器,沾满血迹,案件侦破。执着于每个疑点的马哲仍然想去探究那个烫着大波浪头的女性是谁,他再次找到理发师许亮。
许亮未遂,马哲在医院里的果断签字救了许亮一命。马哲的执着,让他终于揪出那个烫着大波浪头女性的真实身份,原来异装症是许亮誓死要守住的秘密。
案件至此看似真正完结,马哲并没有迎来松口气的时候。他与妻子(曾美慧孜 饰)原本满怀期待孩子的降临,却得到医生告知,孩子有10%的概率罹患基因类疾病,夫妻俩在是否保住孩子上起了争执。祸不单行,命案又起波澜,疯子从疯人院逃出再次杀人,搜捕未果,上级施加压力,马哲已到了不堪重负之时,否则如此痴迷于工作的他不会在关键的时刻提出离职。
出院的许亮来到办公地点给马哲送上感谢的锦旗,俩人的交谈中满是乐观,这一刻也拯救了马哲——仿佛他的工作是有意义的,马哲的脸上终于有久违的笑意。刚走出办公地点,最悚然的一刻发生(这里真的让很多观众吓了一跳)。这恐怕是最后一棵稻草,马哲的内心秩序彻底被击垮。
理性的对立面,如果只是“非理性”,那么理性的坐标系仍然是恒定的,非理性仍然反衬着理性的功能。可如果理性的对立面,是偶然(诗人的偶然闯入),是完全不讲理性与逻辑的疯癫(疯子的杀戮),是不被外界理解、外人也根本无法感同身受的“小众”(许亮誓死对秘密的守护),是微乎其微的概率(大多数孩子都健康,偏偏马哲未出世的孩子有可能罹患基因疾病),是难以捉摸的命运,马哲这才发现:理性在某些时刻的徒劳、无力和虚妄。各种原因的累积堆叠,促成一个理想至上者走向疯癫。
人们自不是怀疑理性的价值,只是,理性的神话长久以来统治着社会的主流观念。人们过多强调理性的严谨、正经与专注,比如马哲井井有条安排着什么时候结婚、妻子什么时候怀孕的人生节奏,不多给那些多愁善感的时刻留下空间,也对于失控的疯癫缺乏应对与心理准备;理性的定义权也掌握在绝大数人手中,社会主流定义着什么才是“正常”,什么样是“不正常”,比如很难想见一个异装症的人在1990年代要面临多大的压力……
物极必反,当理性走向极端,理性看似是在维护正常,却由此压抑小众、催生疯癫,比如许亮最后的自毁;理性看似可以控制生活的所有确定性,不确定的存在反而摧毁了信仰,马哲就是堕入如此境地。
电影中疯癫与理性的辩证法,不免让人联想到如今社交网络中经常看到的“发疯文学”。“发疯文学”这类存在,并非对理性的颠覆,只是放下对绝对理性的迷信;并非对主流的否定,但它允许“非主流”“异类”的存在;并非鼓励戾气的蔓延,但允许情绪的释放和宣泄……“癫狂”从来都是世界的一部分,面对理性至上的压抑,这一代年轻人努力地去找寻自洽的生存之道。
从采访中可知,《河边的错误》的主创者对于审查的边界有清晰的认知,他们在剧本阶段就自动规避了小说文本中一些内容,无法在时代上做太多的显性联系。虽然魏书钧一如既往在电影中留下诸多可供过度阐释的意象,却也应该承认,《河边的错误》具体的时代指涉是微弱的,它的很多深刻依赖于文艺片观众脑洞大开的各种联想(几乎是对电影的二次创作),让解读比电影本身更精彩。
无论如何,电影中疯癫与理性的辩证思考并不过时,类型元素与心理悬疑的结合是不错的尝试,胶片拍摄与气氛的出色营造让电影艺术性很高,繁复的意象有广阔解读空间。《河边的错误》找到它的目标观众就好。